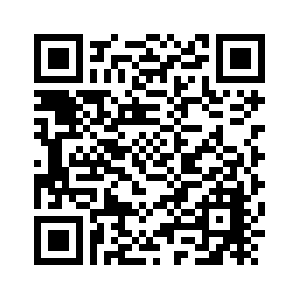Deepseek问世以来,“AI+医疗”的风声一直在延续。近年来,从《“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到《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的发布,政策东风持续助推“AI + 医疗”的发展。DeepSeek等大模型为产业注入新信心,各地知名三甲医院接入国产大模型的消息覆盖了整个春天。
然而通用大语言模型在业务上落地的速度远比媒体报道和资本市场热捧来得慢得多,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对模型的性能和精确度有着最高级别的要求,医院和医生对AI工具的直接应用都保持相当保守的态度,万亿行业有如深海坚冰。
“网上常说AI医疗落地难,从咱们老百姓的视角看,患者还是面对真人医生更有安全感,担心AI出错了没人担责,鲜有人说是因为医疗行业数据质量差。但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内行人的看法。”马国峰作为医众的创始人,已经积累了十年的行业洞察。
去年年底,医众这家已经拥有上千家付费医院客户的医疗数据公司推出了全新的数据AI基座服务,用最简单直接的产品逻辑突破了数据应用的瓶颈,让医院看到了AI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我们和一些三甲医院有长期的探讨,数据科的负责人听到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说这是最正确也是最不可能实现的,”马国峰说,“但也终于眼见为实了。难而正确的事情不白做,我们现在去聊客户也都简单了,随时可以接入做产品验证,医院很快就理解我们的价值。”
医众不是一家趁着AI东风成立的新玩家,而是经历过上一波“医疗AI影像”小风口的低调实力派。他们不靠造势,从不给客户和投资人讲AI的故事,先后拿了金沙江、红杉等机构投资仍保持低调的作风,只是踏实做产品、做交付。在技术进步和客户信任这些复利的积累里持续思考下一步创新的方向和机会。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很清晰,就是做医疗科技进步的催化剂。”这位鲜少面对媒体的创业者近日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医众”创始人马国峰
到冰川之下:做数据层的“底层创新”
新华网: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给我们讲讲医众所推出的AI数据基座这个新产品。
马国峰:简单说,我们做四件事,一是数据的整合和治理。数据质量是AI落地应用最根本的基础,我们把数据的可用性真正交还到医院手里;二是数据的自动化交付。把传统的信息化节点转化成智能模块,在数据层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管理数据的流转,打通AI应用的链路;三是提供一个开放平台让医院去实现医疗数据价值的转化,也呼应政策里常提到的行业数据资产化,这也是医院数据管理模式的演进方向;四是我们提供一个原创科学推理模型的数据智能产品,是结合图技术训练的针对医疗行业和医院场景的小语言模型,有严密的科学推理过程,不依赖算力,CPU就能跑起来用。
从解决现实数据障碍,到让AI替代传统信息化里人工的工作,再帮助客户去实现数据资产的价值转换,这些基础之上,医院会发现AI工具一下子就可以日常“为我所用”了。
新华网:有没有一些现实的例子可以说说?
马国峰:案例太多了,因为我们的产品不是针对某些特定场景,但这种底层的改变可以在各个场景创造出新变化。
比如医院要完成一个传染病数据上报的任务,传统数据团队往往耗费几个月,改造系统,整改数据标准,再抽取数据做集成以及协调厂家做接口开发。整个过程包括后续管理都依赖人工和多方协调。而我们的数据基座,调用模型来生成智能体,一两天就能完成同样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医保的审核,上万条规则多且复杂,很多医院考虑去采购一个单独的系统,但如果用数据基座去解决,结合医院自身数据,医院自己就能维护这些规则,沉淀在系统上成为基座上的知识,拓展模型训练成智能体,无论是日常自查纠错还是指引医生的工作,都是实时可用的。这些都是颠覆性的效率革命。
再比如说医院想改造传统系统,但由于系统耦合性太强了,需要对应系统厂家配合做新开发,成本就很高。如果不能完成嵌入改造,医生也觉得产品和业务流程分离,不好用,这是一个典型的落地难的问题。而我们的数据机器人可以把传统链路上的环节解构为人工智能模块,这个流程直接就走通了,医生日常就能用上。
新华网:市面上被讨论最多的都是应用层的东西,因为大众容易想象和理解,你们做的这个却不是,这里面都有哪些考虑?
马国峰:因为看到了数据质量和性能是医疗行业AI发展的掣肘。目前大多数智能的场景也都是套用大模型,应用在专业垂直领域还是有很大落差。对医疗行业来说,应用都是冰山一角,我们选择到冰山下面去,从底层解决真问题。
我们过去做的影像数据也可以说是应用层的产品,但我们的定位是数据层面解决问题的服务商。因为影像是医院存储规模最大的数据源,做好应用层的本质也是往底层去探索的,当时差异化就在于数据层面的管理和治理。当时也有一些客户提出来让我们做AI模块做智能化,但是我们考虑,数据的质量和性能问题不解决,做AI效率是很低的。
在商业逻辑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可以把产品做到更简单,简单就意味着成本可控,随着业务发展,边际利润会更好。我们不能反复靠人来解决新的问题,而是把积累的经验梳理成知识图谱,用智能来解决问题,只有提升效率,才能在竞争里有质量的生存下去。
新华网:这些问题以前没有别人尝试解决过吗?
马国峰:最接近的可能是一些做数据湖仓方案的公司,他们的路径是抽取数据,转化并存储,搭建和维护成本非常高,而医院业务数据一直在更新,数据仓却做不到实时更新,最后往往变成单一场景数据库,且它的性能很难支持日常临床的业务,医院运营管理层面的数据也往往不准确。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赋能医院的效率和创新
新华网:你们的第一批目标客户是什么样的医院呢,最能理解你们价值的是谁?
马国峰:规模大的医院,因为有懂技术的专业团队,理解非常快。应用的场景多,痛点也更痛,也更能理解我们这个事的门槛和重要性。
很多大医院都有意识在AI领域探索应用,比如之前北京某个三甲医院内部招募人工智能小组,谁有想法都可以去参与产品的创新。像这样的医院与我们基座设计的目的契合度很高,帮助他们解决很多小而麻烦的事,剥离掉脏活累活后,医院自主创新的效率就会特别高,这是我们最想实现的效果。
新华网:所以其实你们对医院是赋能的关系吗?
马国峰:没错,我们从不考虑做AI医生,因为我们不会比医生更懂他们的专业,但是我们想给医生和医院提供一个能力基础,靠自己就可以训练出好的AI。科技公司训练一个医疗AI产品是需要大量的医院临床工作来配合的,尤其是数据标注这样基础的工作都需要医生贡献知识。
我们的初衷就是反向来,更简单直接,帮医院解决最麻烦的事,提供可以本地部署的开放平台,他们可以随时调用这些能力,医院自己就有空间和基础完成应用层的创新,我们来配合做高阶算法。这种开放的心态是我认为AI时代最必不可少的,“功成不必在我”,但我是不可缺少的催化剂,“功成必定有我”。
新华网:这些痛点和需求都是长期和医院接触的过程里了解到的吗?
马国峰:只听需求就做会回到定制化的老路,是没有未来的。苹果手机面世前,没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智能手机。客户基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在提需求时往往预设了解决方式,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我们需要不断的用更新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在行业里持续的洞察去思考出一个最佳路径来满足医院的需求。
新华网:AI数据基座落地之后,可预期的未来还会出现哪些新的机会?这里面有哪些是医众可以做的?
马国峰:当有能力的大医院在我们的平台基础上构建了各种AI的创新,这些新的应用就可以给到不那么具备技术能力的医院,直接拥有应用层的能力;脱敏后的结构化数据也可以更多的用于医疗科研创新。这是医众要支持的价值转化和能力输出。
长期来看,我们虽然身在医疗行业,但数据基座的能力其实是一种通用能力。未来,我们在医疗之外也可以尝试去延展其他领域,凡是有大量跨系统数据的大机构,其实都能用得上。最终希望大家都解放出来去做创造的事情,而不是浪费时间在低效的数据和系统维护上,这是我们做底层创新突破的终极目标。
日复一日的从零到一:传统行业里的创新团队
新华网:这段时间也看到很多大厂现在说要下场做AI医疗,把这当作未来几年的重点,你怎么看呢,这会对你们形成竞争吗?
马国峰:竞争一定是会有的,但我永远相信越是在底层能力,竞争对手的范围就会收窄,应用层可能会有很多新东西,但是底层创新的维度上是很难重复造轮子的。我们花了时间和精力做了难而正确的事情,给医院降低了成本,拓宽了资源,未来的空间是更大的。
新华网:医众的团队和市面上常见的“AI团队”不太一样,你们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马国峰:确实,我们不是典型AI背景团队,但我们做的是垂直产业,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的团队是AI队伍里离医院最近的,时间也足够长,我们的CTO在创业之前也是做医疗数据,他太了解这个行业需要什么。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年做的底层能力构建,是很多高大上背景的团队不愿意也没能力做的。
我花很多时间在思考组织和人的问题,怎么让团队更快成长,不同能力属性的人之间怎么配合。真理至简,说出来都很平淡,就是在明确的原则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给足空间,早先我们就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手册,把公司要做什么,有哪些最基本的原则都写的很清楚,在原则之下不设任何规则,让大家有足够宽松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构建自己的能力。
新华网:怎么能一直做到持续创新呢?
马国峰:放下对过往认知路径的依赖,我们团队内部鼓励平等的辩论,随时验证想法。各地的一线同事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听他们讲一些细节,从细节里提取新的想法和可能性。回到业务模式上,开放就本身就是创新的动力,初期是我们帮助医院去熟悉这些应用,启发他们去拓展新的思路,他们的创新也会对我们有启发,这是开放带来的最大价值。